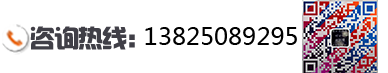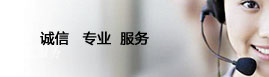2023年可以说是中式恐怖游戏的井喷之年。姑且不论7月发行的《三伏》(拾英,2023)和《无间梦境・来生戏》(下文简称《来生戏》),光是上半年就有《过阴》(漫森,2023)、《戏怨》(勾陈一,2023)、《阴阳锅2》(勾陈一,2023)、《阿姐鼓》(勾陈一,2023)、《残秽的我们2》(Game Logic,2023)、《上坟》(Flower Shadow,2023)、《吃香》(CE-Asia,2023)、《隐秘的角落》(Aluba,2023)等一众作品问世。
可是随着中式恐怖类型化发展逐渐泛滥,相似的元素被反复挖掘,同类型游戏的审美同质化趋势也逐步显现,玩家开始出现审美疲劳与“二创”失焦的情况。眼下,虽然不少作品进行了赛道细分、具有风格差异,例如,现代题材的游戏相当丰富(如民国妻妾、七十年代、校园霸凌、打工社畜),但最出圈和最被跟风的似乎总是“献祭婚配和轮回永生”这一主题。游戏在整体上也随之变得具有强烈的即视感:美术风格雷同、人物建模高度相似、剧情与解谜难以契合、人物动机打磨粗糙,等等。这些评价成为了悬挂在各游戏工作室头上的魔咒。
笔者认为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之一在于,恐怖游戏里的玩家能动性(player Initiative)究竟应该如何与恐怖美学形成吻合,才能既让玩家拥有沉浸(immersion)的游戏体验,又不至于完全沉溺其中,同时还能得到涌现(emergent)的新奇体验。
作为游戏学研究的根本问题之一,玩家能动性一直备受关注。傅善超认为,玩家能动性应该被归到玩家与系统之间的相互承认(reciprocal recognition)概念中,进而达成自在自为的能动性,并生发为“一种否定性与偶然性的经验”[1]。
在中式恐怖游戏里,玩家能动性更为凸显,主要涉及知觉感官与游戏体验形成的缝隙。
从知觉感官上来看,中式恐怖游戏在营造恐怖感/毛骨悚然感上更多依靠视听要素,它们都是无物之阵,这些“反复出现的死亡象征符号(棺材、香烛、纸钱等),指向一段段未经整理的前现代历史,和无孔不入的集体无意识”[2],最后形成没有出口的阈限空间。如此,中式恐怖游戏就对玩家造成了强烈的神经质视觉(neurotic visuality),而不仅仅是西式恐怖作品那样的触感视觉(haptic visuality)——如类似《电锯惊魂》(SAW,2004-2022)那样,大量出现血腥画面形成的生理惊悚(thriller)。
按照克劳斯·皮亚斯(Claus Pias)的说法,西式恐怖游戏更接近动作陈述组游戏(玩家完成打败/逃离),而中式恐怖游戏则更像是冒险陈述组游戏(玩家进行解谜/叙事)。西式恐怖游戏里,玩家可以与血腥的畸形化对象(例如《纸嫁衣》出品方的另一款游戏《黑暗笔录》里出现的克系怪物)进行对抗。
但中式恐怖游戏完全不同,越是完整的恐怖敌托邦,对玩家解谜过程的否定感就越重。如果玩家-角色无法顺利完成游戏,将角色从被压抑物(恐怖物)中释放,那么游戏就会一直在“双重不能”中循环,即“仪式的完成不能/角色的逃离不能”。
“仪式的完成不能”体现在中式恐怖游戏的解谜-仪式关系形成了一组对位关系。主角无论是现代社会都市人,还是仪式里的当事人,都在否定性与偶然性的并置中难以逃离。习俗仪式作为假设的必然性(hypothetical necessity),会最大限度地完成自我主体意志的否定,并通过对个人的压抑乃至抹除,让献祭得以完成。
“角色的逃离不能”则体现在游戏设置中。仪式其实并未真正开始,只是在游戏开始时处于“即将进行”的状态,等待角色的遵循/反抗。这正是戴维森(Donald Davidson)所说的因果偏离(deviant causal chains),只有玩家-游戏的投射关系的叙事偶然性达成之后,仪式才能在必将失败的结局(逃离无物之阵)中获得成功的可能性(游戏通关)。
在中式恐怖游戏的实际操作过程中,还存在玩家能动性的毛刺感(burr-feeling)现象:对“仪式/谜题/线索”结构的疏离。玩家在游戏中最重要的行动就是解谜,解谜一方面对应仪式的完成度,另一方面还必须实现对线索的呈现,玩家不可能在毫无线索的情况下进行游戏。所以谜题就必须兼顾仪式完成逻辑与视觉感知逻辑。
仪式完成逻辑指向恐怖时空或民俗仪式,在完成度上必须辅助大量流程及其背后的知识理论。于是玩家会在中式恐怖游戏里阅读大量记录性文本(书本、新闻、笔记和口耳相传),游戏体感也随之被阅读观感频繁打断。
而视觉感知逻辑则相反,它需要明确可见的提示。于是大量肖似的视听段落出现在同一游戏场景,形成对完成解谜的文本/语义的临近性替换(相似颜色、排列结构、数字提示),甚至不惜营造违和感以完成提示。
本来仪式完成逻辑与视觉感知逻辑就难以兼顾,中式恐怖游戏良莠不齐的质量则进一步加深了毛刺感,使得“仪式/谜题/线索”结构的一致性更加不稳定:在很多游戏中颜色、排列、数字的出场都极其突兀,这直接导致玩家的审美前见(vorsicht)机制发挥作用,频繁出现“轻度闹场不足”,让游戏失去“由外部恐怖氛围转化为内部恐怖审美的体验过程”[3],玩家进而排斥游戏创建的恐怖叙境。当然,某些以量取胜的工作室作品,带给玩家的游戏体验则更加糟糕。
一般而言,中式恐怖游戏面临的困境是双重的,它既是玩家能动性的体验困境,也是恐怖作品的美学困境。
李天语认为,恐怖美学的视觉化主要有三类,鬼魂化、畸形化和外部视觉血腥化/内部精神错乱化[4]。在经过本土化改造的早期中式恐怖游戏作品里,上述情况都有所对应。
鬼魂化对应的是纸与偶,这二者正好都是《纸嫁衣》1~4部系列最常采用的意象。纸的背后是丧葬文化,纸也与烧密切相关,由此形成一种涂尔干(Émile Durkheim)所说的,凝视火焰时产生的仪式性,“将供奉者从与无形神灵的交流中残存、绵延的魔力中分离出来。每一步都是整个仪式过程的一个缩影和转喻(metonymy)”[5]。偶的对应则是非常典型的恐怖谷效应,偶(人偶、木偶)一方面和人身形颇为相似,另一方面又是明确的非人存在,同时还伴有强烈的被命运操控的感觉,这更能激发人的恐惧。《来生戏》中,也首次出现了偶的出镜率远高于纸的情况。
畸形化对应的是异形(Alien),意味着身份识别不能的危险,同时也是主体意志出现碎片,却依然不愿滑向解离的象征。畸形化的谱系学图像就是从奇美拉(Χίμαιρα)到怪兽(Monster)再到科学怪人(Frankenstein)的序列,“是肮脏与不洁、恶心与畸形混杂而成的丑恶感,是尸块与化学组接而成的杀人机器,是重毒毁容下令人作呕的病态形象”[6]。目前这方面做得最精细的中式恐怖游戏就是《残秽的我们2》,里面有大量各种残肢肉块组成的畸形图像。《黑暗笔录》里的最终反派(克系大眼睛与触手)则是畸形化发展到神秘性这一极端的结果。
外部视觉血腥化/内部精神错乱化对应的则是视觉冲击与精神分裂,最常出现的就是光感视觉(optical visuality)恐怖作品。外部视觉血腥化在战争题材的作品中较多出现,内部精神错乱化则与个人心理恐怖作品联系密切,不过,这类风格在中式恐怖游戏里并不多见。
如果说中式恐怖游戏早期的解决思路是依靠题材匮乏带来的先发红利来获得涌现感,那么之后又该何去何从?
《来生戏》游戏海报:仪式与谜题
中篇:作为上位范畴的怪诞美学
在恐怖美学的研究中,传统学术观点将恐怖与崇高(sublime)作为对位关系进行转化。克斯梅亚甚至在《美学重大问题》(Aesthetics:The Big Questions,1998)里,把恐怖(现代)和悲剧(古代)、崇高(近代)相提并论,认为这是所有审美经验类型中,被发现的第三种痛感审美经验类型。康德(Immanuel Kant)就认为,当人们遭遇崇高时,同时也会唤起恐惧的情感。尤其是崇高物从“数量无限多、体积无限大”的可视主体物变为空无空间(empty space)之后,由此生发出强烈的不可言说的压迫性,并逐渐扭曲为病理性的抽象空间,最后褫夺了个体存在的意义感。这也正对应着中式恐怖游戏里无物之阵对角色/玩家的由外而内的压迫。
在伯克(Edmund Burke)与康德的崇高理论中,恐怖作为一种不断剥离怜悯成分的美学体验,与崇高在能动性上形成反差:崇高具有超越感,是主体战胜客体的昂扬情感体验,而恐怖则是更旁观者性质的情感,并不激发行动,恐怖怪物/空间才真正具备行动力[7]。
这就又折返回玩家能动性问题上,并在美学里形成体验悖论:当玩家能动性过强时,会形成两种消解恐怖感的审美体验,超越/反抗的崇高感与充满愉悦的恶意感;而当玩家能动性削弱时,恐怖感虽然重新占据上风,玩家主体意志却也随之剥离。
玩家是否真的逃离/消灭了恐怖?事实上并非如此。无论中式抑或西式风格,大量恐怖游戏都会采用开放式结局以预示恐怖物的无处不在。这种做法虽然有助于作品续集的开发,但正好落入无物之阵的彀中,玩家的努力逃离/消灭过程在文本中也被宣告为意义流失:“日常只是暂时的,新日常彰显的不是安乐,而是周遭随时蛰伏的危险”。正如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所说,恐怖并不是与个体对立的场景,而是被植入的人造假体(prothèse),最后变成如影随形的身体场景(la scène du corp),永远无法被抛离。
与此同时,现代性生活也与恐怖游戏实现了美学逻辑的同构:空无空间指向都市、地铁、广场等诸多现代城市的公共空间;无物之阵指向被精确化刻度的、重复着机械工作流程的、高度相似的格子间办公区场景;恐怖怪物则蜕变为模糊晦暗的大他者,它们是入侵者、毁灭灾难与战争创伤的具象,一直存在于现代性生活的边缘。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就认为,我们根本无需在恐怖游戏里寻找恐怖美学体验,因为所处的现实生活早已形成集体梦魇:它无法被真正祛除,只能在游戏中被改写为外来者,继而被想象性地解决。
当恐怖美学难以获得玩家的青睐时,我们应该转向寻求其上位范畴怪诞美学(grotesque aesthetics)的帮助。
从16世纪被发现的尼禄金屋(Domus Aurea)上的洞穴装饰画开始,怪诞只是作为一种绘画风格出现。直到19世纪末,沃尔夫冈·凯泽尔(Wolfgang Kayser)在《艺术与文学中的怪诞》(The Grotesque in Art and Literature,1957)中对怪诞进行明确界定后,怪诞才正式从类型风格转变为“既可怕又可笑”的审美范畴。
正因为最早的发现地是洞穴(grotta),所以怪诞(grottesco)的词根与洞穴密切相关。据说拉斐尔最擅长绘制怪诞画作,其主要特征是生物(人、植物、动物)与非生物(器物、建筑)混杂对接生长、面容和行为毫无表情(更像旁观者而非受害者)、强烈写实且毫无理由的共存画面,以及既让人害怕又让人好笑的对立统一整体感,但与此同时画面又相当典雅纯净,毫无残损、血腥、肮脏等强烈的视觉形象。这就导致怪诞图像并无任何隐喻学含义,似乎作者既不知道为何要如此绘画,也无法指称任何画外之意[8]。
随着这种类型化风格的流行,原初的怪诞获得了完整的审美范畴,形成现代怪诞。现代怪诞总共有四个要素,分别是“滑稽与恶的构成成分,可怕又好笑的接受反应”。雨果(Victor Hugo)在《克伦威尔·序》里更加清晰地总结道:“怪诞一方面创造了畸形(difforme)与可怕(horrible),另一方面创造了可笑(comique)与滑稽(bouffon)”[9]。这意味着怪诞在美学史上首次获得了明确的阐释,形成了恐怖/可怕与滑稽/可笑的双重交互机制。
怪诞美学意味着一种撕裂又统一的审美风格在陌生化的构成方式上达成了一致,怪诞作品也随之具有能覆盖恐怖作品的功能。怪诞作品因为邪恶感与滑稽感共同存在,所以成为“正在/驱逐邪恶”的场景:“驱逐邪恶”意味着行动主体的意志,“正在进行”则意味着邪恶无处不在。所以斯泰格(Michael Steig)就认为怪诞在心理学意义上存在释放性与压抑性并置的悖论,这是“精神分裂症身体的片语”(an anagram of the schizophrenic body):怪诞在消除焦虑的同时,源源不断地制造焦虑。
由此,后现代恐怖(即怪诞)实现了从制造噩梦阶段,到生成噩梦,再到抑制噩梦阶段的转变。
制造噩梦是恐怖世界的隐喻,是震撼性视觉冲击的恐怖物。这些恐怖物拥有主体意志,作为怪物(monster),它们拥有自己的叙事体系。角色遭受恐怖体验往往是因为误入了它们所在的世界,在完成逃离/打败恐怖物的行为之后,恐怖故事便宣告结束。
生成噩梦与人的异化密切相关,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人性解离的投射,是精神症状躯体化与创伤经历的重现,这意味着“由外在形象的丑陋,转向人类内在心灵和精神世界潜意识的可怕欲念”[10]。
抑制噩梦则通过各要素的扁平、拼贴与过渲染的方式,让角色/玩家在恐怖作品里形成游戏感,作为网络原住民的玩家,早已对拟像世界脱敏。此时,后现代恐怖几乎可以等同于怪诞,游戏中的交互/旁观带来了滑稽/可笑,同时又以强烈的疏离营造出恐怖/可怕。
表1:恐怖功能与噩梦的三阶段关系
怪诞中的“滑稽/可笑”功能与“恐怖/可怕”功能相互作用,于是“中式怪诞游戏”就随之诞生,《来生戏》就是从恐怖美学向怪诞美学转型的尝试。
《来生戏》游戏海报:陶梦嫣的童年阴影
下篇:怪诞美学的“来生戏”
《纸嫁衣》系列不再以数字编号作为作品连续的标记,7月出品的游戏名是《纸嫁衣无间梦境(上)·来生戏》。其中固然有游戏版号的原因,但《来生戏》确与《纸嫁衣》系列呈现出明显的美学差异。虽然有相似的元素、六葬/纸新娘的世界观和仪式等一干类型化叙事,但《来生戏》作为“中式志异民俗解谜”游戏[11]实现了对恐怖美学的超越,投向怪诞美学的怀抱。
其实早在《纸嫁衣》1~4中,已隐约有怪诞美学的影子。即道具获取界面里会附上简短介绍,有时是作为仪式用品的知识扩展,有时则是主角的吐槽。而被反复消解恐怖感的梗则是“六葬菩萨的头又掉了”,这一举动被游戏方重复多次后变成了解构意味浓烈的鬼畜。《纸嫁衣4·红丝缠》的最后甚至打出一行字幕“本片拍摄过程中,没有任何六葬菩萨受到过伤害”。
在与前作相似的部分上,《来生戏》对恐怖感的消解程度变得更为强劲。角色(陶梦嫣/荀元丰)拿到道具后,UI界面信息栏中的吐槽力度不减反升。其中既有(荀元丰)对解谜过程无知的困惑,也有(陶梦嫣)对仪式重复进行的不解,由此与随处可见的仪式文本形成鲜明对比,这就导致在游戏的互动环节可以随时稀释恐怖感的“纯度”。已经形成大他者符号的六葬菩萨,在本作中更是被以各种方式有意无意地祛除神秘性。
《来生戏》在“滑稽/可笑”和解构恐怖的设置上更加别出心裁,形成了一套结合网络互动行为、后现代人类视角和个人精神症状与古老仪式契合的怪诞美学。
《来生戏》游戏截图:陶梦嫣的解释
滑稽的发出者:《来生戏》的玩家视角
《来生戏》玩家从一开始就扮演着与恐怖美学游戏相异的三位主角,他们分别是钟梓萓(成熟玩家)、陶梦嫣(反复攻略者)和荀元丰(无记忆新手)。这三人分别对应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理解前结构(Vorverstandnis)[12]的前见、前有和前设概念,在怪诞美学中占据“滑稽/可笑”的功能,所以他们在游戏前期(第1~3折)几乎不受到反派屠浮生所营造的幻戏,即“剧场/梦境/仪式”三层嵌套的干扰。
钟梓萓具有前见-玩家能动性(vorsicht-player initiative)。她不熟悉纸嫁衣祭祀,且自始至终拒绝接受这套恐怖叙境。但她很熟悉中式恐怖游戏的操作方法,频繁援引桌面悬疑(desktop suspense)[13]的游戏体验,并将其解释为恶作剧、游戏、密室逃脱、摄像头、大型剧本杀和节目效果。钟梓萓虽然不是玩家可操纵的对象,却极具游戏性:她天然具备“上门开锁、维修家电”的能力。无法打开的关键道具由荀元丰交给钟梓萓后,很快就被她以暴力手段破除。钟梓萓的能力几乎可以与“偏向于游戏化体验的操控感与驾驭感,将恐怖元素设想成游戏化的虚拟任务或物品”[14]的能力画等号。玩家作为代理行为者,也正是钟梓萓的感觉主体:玩家正是在游戏中扮演了能解开任何谜题的能动者。
陶梦嫣具备前有-玩家能动性(vorhabe-player initiative)。她是二度出现的可由玩家操控的女主角(首次出场为《纸嫁衣2:奘铃村》)。所有祭祀仪式对陶梦嫣来说都是前有的一部分(包括纸新娘故事、个人童年阴影、游戏机关与谜题设置),陶梦嫣也顺利承担起熟知故事的GM(game master)角色。陶梦嫣采用速食电影(snackification movie)解说法给其他两人扫盲:以“注意看,这个女人叫小陶”开头,以高度形似短视频界面的“图片快闪口述”为风格,将纸新娘与奘铃村的故事以“如同叙述者的身份参与电影(纸新娘)的再次建构,从而获得间离效果”[15]。陶梦嫣在前期借用了自己的角色符号(化名小翠,新手引导角色功能),并通过先于叙事的观看行为(她在剧院后台通过行动指引荀元丰解谜)完成对自我的戏仿,同时也消解了中式恐怖仪式的无物之阵(游戏机关的解开并不是因为遵从/反抗屠浮生的幻戏仪式,而是源自陶梦嫣的引导)。
荀元丰具有前设-玩家能动性(vogriff-player initiative)。荀元丰是梁少平的转世体,而不是记忆体。荀元丰作为从植物人中惊醒的模样,缺乏自己的记忆,是一个非本真存在(inauthentic existence),直到概念框架系统(梁少平主体意志)附着以后,才作为本真存在(authentic existence)形成自主意志。在游戏过程中,由于荀元丰对外界一无所知,前作通过拍照就能窥探鬼影的手机——作为“现代性个体所能掌控的科学,被设想为高于且终将阐明、征服不可言说之物”[16]的设定——在本作里变成了“砖块”。荀元丰在解谜时一直处于畏惧(Angst)状态,频繁陷入无家可归(nicht-zuhause-sein)的自责无用情绪。这也导致在本作的荀元丰在游戏对话中出现大量由括号框住的没有对应配音的内心独白。不过,这些独白并不是创伤性记忆,而是对游戏恐怖感的失焦。
前见、前有与前设的“滑稽/可笑”功能共同形成对《来生戏》“恐怖/可怕”功能的背离:前见(钟梓萓)消除了剧院恐怖感的梦核(dreamcore)空间,转向游戏刺激感体验;前有(陶梦嫣)重新进入相似环境,消除了恐怖生成的陌生感;前设(荀元丰)的母本(梁少平),祛除了恐怖仪式(剧本《梁少平之死》)作为改写摹本的独特性,使其沦为“玩物”。保罗·纽曼(Paul Newman)甚至认为,随着影像与游戏行业的持续发展,恐怖发展史已经进入第四阶段,即讽刺剧或喜剧期[17],以《林间小屋》(The Cabin in the Woods,2012)最为典型。
理解前结构同时具有很强的主体能动性,作为玩家能动性在游戏外的意向性补充,引发了对游戏审美期待的超越。视网膜能摄取的信息毕竟有限,游戏的屏幕空间(screen space)形成二度视网膜,让“给定事实变得贫乏”,而注视所形成的信息“包括过去经验所产生的对物体的知识”[18],最典型的就是两歧图形,这就是前理解结构在发挥作用。同时在中式恐怖游戏解谜过程里,大量两歧图与视差图也成为祭祀仪式完成之外的线索提供。
《来生戏》游戏截图:陶梦嫣被困在屠浮生的幻戏中
恐怖的生成者:《来生戏》的人格解离
《来生戏》用三位主角理解前结构行动,以“抑制噩梦”的怪诞美学宣告“制造噩梦”的前现代恐怖美学模式的失效。于是游戏另辟蹊径,重新将视角放在“生成噩梦”上,大量引入精神症状障碍与人格解离的内容。正是因为有滑稽/可笑功能的反衬,怪诞主题中的“恐怖/可怕”功能在这两折内容中,形成了内生性,而不是旁观/交互性,因而更加具有创伤性记忆的恐怖感体验。
在很多不具备怪诞感的恐怖作品里,那些生成的各种怪物都是现代性的具象构建,而不是个人性的精神构建。一方面它们的形象被滥用和拼贴,成为景观社会用以娱乐的一部分,甚至成为“怪物充斥的时代背景”;另一方面这些怪物拥有属于它自己的故事,不再是可消灭/逃离的他者,而是可对话的没有恐怖感的主体。
所以当这些现代性产物-怪物是以群体分发的方式进行时,自然就会产生怪诞美学里的滑稽/可笑感,人们甚至还可以援引科学解释彻底消除其存在的物理空间的合法性,这也与《纸嫁衣4·红丝缠》中崔婉莹(新闻编辑)和张辰瑞(民俗专业研究生)的行动一致。
在加入大量“滑稽/可笑”的设置之后,《来生戏》认识到形成恐怖感的绝非只是外在的视觉奇观(前现代恐怖),还有与角色精神症状的相互呼应(现代恐怖),以及二者之间的跳转(后现代恐怖/怪诞美学)。所以无论是(梁少平之死、陶梦嫣之梦)戏的表演还是(剧场探密、心理调解、镜中法阵)剧场的设置,都在承载了对恐怖物的构象与叙事的同时,又变成只针对陶梦嫣个人的幻戏恐怖叙境(diegetic),形成恐怖主体与恐怖对象的反身同构,并且将这种构象方式剖露出来。
这不再是由恐怖美学驱动的游戏体验,而是由怪诞美学驱动的游戏体验。
钟梓萓在第4折丧失了前见-玩家能动性。于幻戏里被屠浮生重置为心理医生。钟医生直接点出陶梦嫣不稳定的人格解离倾向,甚至有向边缘型人格障碍(BPD)转移的风险,她将陶梦嫣作为前有-玩家能动性的行为全部解释为个人心理问题症状:
“木偶、皮影、童子、陶人……这些你在奘铃村真实见到的东西,形成了记忆表象,而你的潜意识把这些表象合成了幻觉……通过戏台和监控观看别人的故事,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你需要将自己剥离出来才会有安全感,你渴望亲密关系,同时你又害怕被他们伤害。你经常看到蝴蝶,是经典的庄周梦蝶意象,是潜意识在提醒你这是梦境。但你的意识刻意回避了这些不自然,把它们加工成了所谓谜题。你拒绝听到外界的声音,所以我通过镜子来进行催眠治疗,让你的意识和你的无意识对话,这样你才能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
《来生戏》游戏截图:钟医生的精神分析言论
这段钟医生的精神分析,再加上第4折反复出现的罗夏墨迹测验,为《来生戏》中的纸新娘仪式和剧院经历给出了除仪式之阵与幻觉体验的第三种解释,即 “生成噩梦”的解释:精神问题充斥于空间的现代恐怖,恐怖美学中的“消灭/逃离”功能再也无法驱散恐怖感。
罗夏墨迹测验也变成取代“仪式/谜题/线索”的结构疏离和产生双歧/视差图的线索,提供了另一种相当取巧的解释,那就是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所说的“创伤性神经质”里产生的对危险情境的焦虑反应,同时又在梦境中被凝缩和重置为视觉上毫无逻辑、行为上符合仪式的谜题。
所以,当第1~3折的剧院所呈现的幻戏出现在陶梦嫣眼前时,她不为所动,甚至还能成为GM直接切割恐怖感,这正是怪诞美学中“滑稽/可笑”机制的作用。
而当所有谜题都以精神分析而不是仪式完成的模样出现后,陶梦嫣却陷入强烈的分离恐惧之中。
陶梦嫣的人格解离倾向在钟医生的心理诱导之下逐渐扩衍,最后形成具有强烈精神伤害性的梦核空间,并以强烈创伤性回忆组建出回转伤核(carousel-traumacore)。到第5折“梦焉”,梦嫣/梦魇作为同音异构词,在幻戏下实现了“身体=空间”的现代恐怖感。这种恐怖感正是被“滑稽/可笑”所唤醒的“恐怖/可怕”。
如前文所说,鬼魂化对应的是纸与偶。纸嫁衣前作里偶是对前世经历的复现,用以引发主角坠入恐怖惊吓的过往故事,主角是扮演回到前世的玩家,就如《来生戏》前三折中的偶剧(Puppet drama)。而在第五折中,陶梦嫣在屠浮生的幻戏下再现了童年阴影,她被困于自己的过去经历之中。在她的梦魇里,所有其他人都被非人化,木偶也不再是屠浮生操纵的抽象容器,而是一直围绕在陶梦嫣身边的记忆群像投射体。陶梦嫣的形象也随之分离为不同的偶具——有一直被束缚悬挂的纸新娘木偶(puppet),也有被凝缩在童年经历里的布偶(cloth puppet),还有在天平两侧作为解谜物的玩偶(doll)。
荀元丰最后将陶梦嫣从梦魇中解救出来,通过扮演经典京剧《挑滑车》中的长靠武生岳飞,最终把回转伤核变为童梦藏身所(cozy child hideaway)。陶梦嫣也成功从“像旁观者一样看到这个故事”的角色转换为荀元丰的救赎者,两人对彼此故事形成交互,破除了“无助的旁观”所带来的绝望感。
当陶梦嫣从梦魇中醒来之后,“恐怖/可怕”的人格解离危险在“滑稽/可笑”机制下被成功解决。陶梦嫣与钟梓萓拿回属于自己的前理解结构功能,开始对屠浮生一唱一和说起相声,陶梦嫣甚至做出了打破第四堵墙的举动:跳起来直接扔掉游戏界面的血条,也彻底扔掉了角色会扣血的死亡焦虑。
怪诞美学正如凯泽尔所说,是异化的世界。这种异化不仅仅指向现代性语境下的异化,还指向身体造型的异化与个人精神的异化,是“通过赋予机械物生命和剥夺人的生命而达到的”,所以我们在怪诞作品中经常会看到“人变成傀儡、活动木偶和机械人,脸凝固成了面具”。当面具最后取代脸的位置,就会成为怪诞世界中的一部分:“怪诞所倾注的毋宁说是对死亡的恐惧,还不如说是对生活的恐惧”[19]。前者对应的是荀元丰的恐惧,而后者对应的是陶梦嫣的恐惧。
但生活恐惧很快会被“滑稽/可笑”解构,这是怪诞美学的第三重异化,那就是自我/他者的异化,原本自我/他者是望远镜式的体验(the telescoping of experiences),是一块相互投射的连续认同主体,但“交互/旁观”游戏行动将二者切开,使自我与他者不再是“大陆的一片,整体的一部分”,而是可以随时成为交互或旁观的过程。
这一过程的符码正是本文频繁出现的“A/B”结构,它意味着原本连缀的主体(AB)被切割(分离又无法独立的恐怖/可怕),但切割又作为“/”出现在被分离的二者之间形成新的表述(强行嵌入的滑稽/可笑),“/”也成为既可笑又可怕的怪诞存在。
所以《来生戏》以既可笑又可怕的游戏体验,在玩家能动性上实现了从恐怖美学向怪诞美学的转型。陷入庞大的纸嫁衣祭祀仪式/解谜故事中的角色们(钟梓萓、陶梦嫣、荀元丰)进行的就是一场(可以被解释为幻觉、科学、精神错乱以及阴阳世界的)怪诞游戏。这场游戏在交互/旁观中以玩家能动性穿梭于各自的精神空间中,通过滑稽/可笑的美学功能作为一种文化症候群的解释,怪诞/来生戏就是“唤出并克服世界中凶恶性质的尝试”[20],这也是一场无间梦境(phantasms)中的自我冒险之旅。